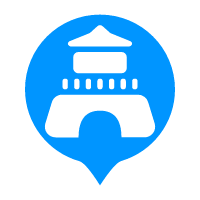- 本期故事关键词: 珠峰 -
有生以来,我第一次触摸到死亡,死亡就在我的眼前,稍有不慎,我就会成为一个冰人,一具尸体。
-1-
在西藏做气象员二十余年,发生过很多事,可唯有下面这件事,因为关乎生死,让我终生难忘。
有一次,康世昌一行人要去珠峰,来回 6 天。在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,我找边增局长请了假,找其他同事帮忙代班,准备一同前往。
几天后的一个早上,我们出发了。路并不好走,最主要的是翻山越岭,一道弯接着一道弯。虽说相距 90 公里,但望山跑死马,实际的路途要远得多。
下午,我们到了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大本营,这个大本营其实很简单,在河滩上支起的两个大帐篷,就是他们临时的办公和生活居所。地方拥挤了点,窄了点,然而在荒郊野外,在珠峰脚下,足以让人心满意足。
驻扎在这个大本营的基本都是甘肃老乡,在海拔 5200 米的地方见到老乡,我觉得分外的欣喜。第三天早上,我还在被窝里惬意地享受着温馨,就听到外面有人说:“早晨的珠峰,真是漂亮!”被这句话叫醒,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猛地爬起来,胡乱地穿上衣服,冲出帐篷。
珠峰,真真切切的珠峰,她现身了,在我眼前毫无掩饰地出现了,早霞披在她身上,那样雄伟壮观和美丽。
吃过饭,背上相机,我和彭开军一同出发,我们想距珠峰更近一点,我们想看珠峰更真一点。

沿着登山队、科考探险队走过的路,我们出发了。也许是一腔豪情的鼓动,也许是在海拔4300米的定日县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的缘故,我竟然没有感觉很累。不多时,我们就追上了前面的台湾同胞,黄校长笑着说:“好轻松,好潇洒哦!”
打过招呼,我们一路向前走去,面前有两条路,一条是上山的路,一条是沿山脚去冰塔林的路。没有向导,我们俩自己决定,抄近路,选择了后者(事实证明,我们这次选择是错误的)。
约莫十几分钟后,一条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,沟下是湍急的河水。几乎没有太多的考虑,我们便决定翻过这条沟去到对岸。水流很急,也很冷,赤足过河是不行的。终于,彭开军找到了一个好的渡口,中间有四块大石头,凭着我读书时期的过河经验,绝对过得去。我站在第三块石头上,要扶彭开军过来,但他的鞋底被磨平,石头上全是冰,太滑,过不来。
这时候,我要退回去已不太现实,要跳到第四块石头上,非得有一股冲劲不可。
低头一看,下面是一块很大的石头,一旦踩空,就会被水冲走,撞在巨石上。我鼓足劲,跨了过去。没想到,我的珠峰之旅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探险。告别了彭开军,我独自一人继续赶路(事实证明,没有结伴而行,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)。
越过河沟,视野无限开阔,眼前的景致很美。由于水流声太大,我指了指山上,又向彭开军摆了摆手,示意他与台湾同胞一块走,毕竟他们有向导(事后我才知道,他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)。
当只剩下我一个人时,我也有点后怕,但我相信自己在天黑前能赶回营地,就没有太在意。这时,我发现自己只剩一点茶水和一罐饮料了,在独自一人时,水显得非常珍贵。
-2-
14:00 ,我已经很累了,而此时,踩出的路已经看不到了。由于山体滑坡,路被乱石占据,脚下有的只是大小不一的石头,一脚踩不稳,就有连石头一起滚到山沟的危险。
抬眼望去,冰塔林并不遥远,这是我心中的希望,也是促使我前行的动力。已是 16:00,该是返回的时候了,可是那美丽的冰塔似乎已经伸手可触了,这种诱惑实在太大,它驱使着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沙丘,此时,我已经滴水全无,身体极度疲乏,就这样翻过了很多沙丘,走走停停。
17:00,我抵达冰塔林,夕阳斜挂,映照在这一座座冰塔上,它们简直就是美玉,洁白无瑕,晶莹剔透,塔缝中因折射而发出蓝色的、翠绿色的光,让你仿佛置身于水晶宫中,周围是颜色各异的宝石。整个冰塔林又非常广阔,如同澎湃着浪花的大海。
我用空的易拉罐盛上潺潺流淌的溪水,不料从珠峰流下的水竟如此甘甜,我一次喝下了十几罐溪水。然后,把水瓶和易拉罐装满溪水,歇息了一会,我准备返回。我知道返回的路在哪儿,我能找到。
然而,走到半山腰时,我却悲哀地发现,自己把相机落在了冰塔林……那是康世昌借给我的胶片相机,价格相当于我当时 3 个月的工资。当我找到相机,再次沿路返回时,已是19:00。这时,天开始下雪,能见度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降低,刚才还在咫尺的珠峰一下子不见了踪影。但让我欣喜的是,我找到了路,刚才在冰塔林中每走 10 米就要歇息一两分钟的我,竟然能连续走 50 米、100 米,甚至 200 米后再喘口气休息。
在返途中我看到一个宿营地,那是登山队员扎营的地方,有幡旗,有石头垒起来的简易的灶台,还有煤气喷灯熏黑的痕迹。这时,我明确地知道,自己走到了真正的登山队行走的道路上了,我有希望赶回去。如果在天黑前能赶上台湾游客,如果在天黑前能走到我熟悉的道路上,哪怕走到凌晨一点、两点,我也要赶回去。
当我再往前走时,路并不好走,与来时的路差不多,视野之内,全是大小不一的石头。在极力找路时,玛尼堆救了我,给我带来了好运气,这些石头成了路标。大石块上垒叠着小石块,它的旁边就是登山队员、科考人员和牦牛走过的小道,我终于抓住了足以让我欣喜若狂的“稻草”,沿着这不时出现的石头叠起的标记,拼命向前狂奔……

20:00,鹅毛大雪开始铺天盖地地落下来,我依然在拼命地赶路,因为我心中存有一线希望。
慢慢地天黑了,又到了中绒布,满是石头,看不清路,这时我心头的希望破灭了,而我也不得不理智地停下来,找一个过夜的地方。
就在我停下来的地方,不远处有一块巨石,下面有一个缺口,走近一看,一只老鼠知趣地逃开了。我搬走下面的小石头,又用石头堵住两边,平着将身体挪进洞里。我在洞口放了几块不小的石头,作为我的防御工具。这个一米多长,三十几厘米宽,二十厘米高的洞,的确“仅容一人居”。
没有遮风挡雨的帐篷,石头缝里吹进的寒风依然刺骨,有水不住地沿石头滴下,有雪飘进洞里;没有被褥,睡着石头,枕着石头,石头很冰冷;没有光明,没有火把,在这石头山上捡不到一根柴火,找不到一点燃料来取暖;没有食物,水也已经喝完,没有供肌体活动的能量;没有找到一个人,没有一声安慰,哪怕是有一个同病相怜的路人,让我们彼此扶携、彼此靠体温战胜这漫漫黑夜也行。
然而,没有,这一切都没有。
如果那晚无雪,有星光、有月光,我也可以靠这点微弱的光赶回去;如果我出来时带了手电筒,我会沿着玛尼堆,找着路回去;如果我带足了食物和饮用水,我会有足够的体力争得时间,最少也可以增加战胜这寒冷的能量;如果我不因折回冰塔林找相机而浪费时间、消耗体力,现在我也该走到那条熟悉的路上了;如果我不贪赏冰塔林,早点返回,这时我已在那温暖的帐篷里了;如果我跟着台湾同胞,跟着他们的向导也不会迷失方向。
如果……没有如果,我被黑夜吞噬,在荒原中孤单无助。
夜很黑,天很冷,人很困、很累、很渴、很饿,躺在这狭窄的“石洞”里,听得见很响的流水声;听得见因山体坍塌滚下山沟的石头,发出的巨大声响。我真想睡,然而我不能睡,因为这一睡可能将永远不能再睁开眼睛;我很想回去,然而我不能,因为一脚踩空,我可能与石头一同滚下山沟,最后粉身碎骨,也可能滑进四面皆冰的冰湖里成为冰人。
有生以来,我第一次触摸到死亡,死亡就在我的眼前,稍有不慎,我就会成为一个冰人,一具尸体。
-3-
羽绒服已经被雪淋透,我冷得发抖,那时,我身上还有一包烟,一盒火柴。
我不想抽烟,但我划燃了火柴,那微弱的光芒映射在石头上,然后迅速熄灭,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和黑暗。我再划燃一根火柴,一点微弱的光芒又迅速出现然后又迅速熄灭。在这样寒冷的夜晚,这一点火焰只有光亮,没有温度,你感受不到它的温暖,因为我置身在一个天然的“冰库”中。
我想起了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,她也曾划燃火柴,但那样的光焰,并不能驱逐寒冷。
我还想起了鲁滨逊,他的处境也不过如此吧,但相比之下,他遇到的寒冷比我要少,况且海中还有鱼,树上还有果。而我所在的海拔5800 米处,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,只有冰冷的石头。我听康世昌说这里曾经出现过雪人,它的脚掌比一个初生婴儿的躯体还大。如果它真的来了,我容身的石洞上的这块巨石也会被它轻易地掀翻。好在人们只是见过雪人的脚印,谁也没有亲眼看到雪人,但愿雪人只是一个传说。
尽管如此,我还是在洞口放置了几块可以投掷的石头,如果真的有猛兽,石头也许没有用,但至少能给我壮壮胆。相比之下,老鼠的生存能力似乎更强,在海拔 5200 米的大本营,它肆意地踩在我的脑袋上,在海拔 5800 米的这里,这块巨大的石头之下居然还有它们,再高的海拔上还有它们吗?
我不知道,但它们的生存能力实在太强。
凌晨 1:30,雪停了,天上依稀有几颗星星,经过雪的映照,已经能看见路了,而停雪后的天冷得让人难以招架,我索性爬起来赶路,仅凭这点星光,我走了一个半小时。这时我又找不到路了,几颗星星又重新隐入云层,我不敢再往前走,停下来试图向下盲探,但在向下滑了几米后,我发现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,因为坡太陡,陡到只要失控,你连抓住草根的机会都没有。
理智再一次战胜了盲目的冒险,我停下了脚步,在一块稍微平坦的空地上停了下来。就这样坐一会,站起来走一会,又坐一会……我不能一直坐着,坐着我都可以睡着,然后被冻僵,成为一尊雕塑。我必须隔段时间走一会儿,以保持我身体的热度。
不知道坐了多久,走了多久,我终于等到了黎明。
7:30,天开始蒙蒙亮,这时我决定找路,先下山再说。可是,当我走下山,看到我来时渡过的那条河,水深且急,要想过河,是一种巨大的冒险。
无奈之下,我沿着河沟上山找路,明明对岸就有路,可是却因一河之隔而不能到达对岸,此时的小雪变成了鹅毛大雪,上山体力消耗太大,走几步就要歇一会,这样走了一小时,我才发现要绕过这条河,按照我现在的速度,最少也要五小时。
于是,我决定渡过这条河。不远处,水流因石块分成三股,河面较宽,水流相对平缓,而且大石块也较多,我决定就从那里突破。好不容易过了河,爬上山沟,太阳出来了,照在身上,我信心倍增,很快就走到分岔的路口。
一路上,我吃雪水,并在杯子里装满了雪,那雪水的确润喉,但后味特苦。距大本营一半的路程时,我意外地发现了自己人,他们也看到了我。我向他们招手,他们朝我冲了过来,彭开军喊着:“说句话呐!”然而我已经喊不出来了,即便是说话,声音都很小。
从昨天 10:30 到现在的 12:30,26 小时,我只吃了半碗汤和半块饼,饿了就靠溪水和雪水来维持。
实在太累了。
司机刘大胡子率先冲到我跟前,抓住我的手,这一刹那间,激动、感动、愧悔、喜悦、悲伤,百种滋味涌上心头。刘大胡子在摸我的脉搏,我孱弱地说:“好着哩,一切都好着哩。”这时,康士昌背着水和八宝粥,彭开军拿着绳子,观测员小刘拿着铁镐赶了过来。看到我,听到我的声音,他们紧绷的神经才慢慢松弛下来。
我吃了一罐八宝粥,喝了一瓶水,体力渐渐恢复,竟跟随着伙伴,一路没有歇息,直奔大本营。
-4-
听他们讲,大家从昨天晚上八点开始一直找到今天凌晨四点,但都没有找到我。回到帐篷,小彭一句话也没说,拿烟的手一直在发抖,今天早上起来,管后勤的黄师傅做了稀饭,大家都没心思喝,还是出来找我,做了各种设想和推断,预备了好几个方案。登山协会的两个人也过来了,等我的消息,见我平安地回来了,他们才放心地离开。
在他们的推断中,最大的可能是,我滑进了冰坑。

这两天的经历实在是谁也料想不到的,大家一直以为我不能活着回来了。生命原本如此脆弱,在大自然面前,人类显得如此渺小,如此单薄,然而人类的智慧终于战胜了自然,在这一过程中,重要的是我战胜了自己,战胜了畏惧的心理,战胜了脆弱的感情。
从这一点上讲,人又是坚强的,生命也是顽强的,并不容易被摧垮,也不会轻易放弃。
结束珠峰之行时,我思潮澎湃,再次回到这块熟悉的土地上,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,一场噩梦。等到梦醒时,梦中的光怪陆离、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,都复归于平静和自然,只是心中永远无法忘记这段经历。
-END-
本文节选自|《那些年,在西藏看“风花雪月”》
作者|王元红

图片|《南极之恋》剧照